《内陆帝国》剧情介绍
内陆帝国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在由金斯利(杰瑞米·艾恩斯 Jeremy Irons 饰)导演的电影里,尼基(劳拉·邓恩 Laura Dern 饰)扮演了一个名叫苏珊的女人,她在剧中的情人是戴文(贾斯汀·塞洛克斯 Justin Theroux 饰)所扮演的比利。 关于这部电影,有一个传说,最先拍摄这个剧本的剧组遭遇了一些可怕的离奇经历,导致电影流产。尼基有一个控制欲爆棚的丈夫,在丈夫给予的巨大压力下,尼基在潜意识里躲进了苏珊这个虚构的角色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奇怪的人出现在了尼基的身边,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件接连发生在尼基的生活里,而尼基呢,在混沌和迷惘之中,她已经无法分辨,自己究竟是尼基,还是苏珊。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七小罗汉浪女大厨第五季弗雷斯诺存酒人我的孩子我的家法医密码永生羊下辈子我再好好过第一季先生,你哪位马大帅3梦想越走越近猎龙王星际旅行:进取号第三季鲁邦三世TheFirst在我们死去前第一季星河战队2:联邦英雄梦幻飞船困斗99号囚室我的秘密城堡蝎子王2:勇士的崛起复仇女黑帮怨灵岛之决不饶恕乘船而去匹诺曹大冒险家法医秦明之幸存者自然城市这不是我潜行吧!奈亚子RememberMyLove(craft先生)凶宅怪谈2
在由金斯利(杰瑞米·艾恩斯 Jeremy Irons 饰)导演的电影里,尼基(劳拉·邓恩 Laura Dern 饰)扮演了一个名叫苏珊的女人,她在剧中的情人是戴文(贾斯汀·塞洛克斯 Justin Theroux 饰)所扮演的比利。 关于这部电影,有一个传说,最先拍摄这个剧本的剧组遭遇了一些可怕的离奇经历,导致电影流产。尼基有一个控制欲爆棚的丈夫,在丈夫给予的巨大压力下,尼基在潜意识里躲进了苏珊这个虚构的角色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奇怪的人出现在了尼基的身边,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件接连发生在尼基的生活里,而尼基呢,在混沌和迷惘之中,她已经无法分辨,自己究竟是尼基,还是苏珊。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七小罗汉浪女大厨第五季弗雷斯诺存酒人我的孩子我的家法医密码永生羊下辈子我再好好过第一季先生,你哪位马大帅3梦想越走越近猎龙王星际旅行:进取号第三季鲁邦三世TheFirst在我们死去前第一季星河战队2:联邦英雄梦幻飞船困斗99号囚室我的秘密城堡蝎子王2:勇士的崛起复仇女黑帮怨灵岛之决不饶恕乘船而去匹诺曹大冒险家法医秦明之幸存者自然城市这不是我潜行吧!奈亚子RememberMyLove(craft先生)凶宅怪谈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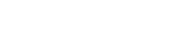
混乱、无序、如坠梦境般难以理解,是林奇没错了。
林奇的片子看到这部 实在有些受不了
不是用来“观看”,而是用来“感受”的电影。
邓恩老了,林奇疯了,我输了…一百分钟退场,还是汉拿山的烤肉最香~~~
没看懂
对不起我看不下去了 看到第37分钟
这个是我目前最看不懂得电影
我在分成几瓣,我在流泪,我在梦境里不断沉沦。所以观众在解密,导演在狂笑。
很神经的片子,看了两小时还有一小时左右片长,实在看不下去,放弃!
好诡异的片子,完全没看懂
250422@天幕新彩云云里雾里,不过一定会再看的。
林奇的片子基本都是一个套路,但是这部自始至终都相当恐怖和诡异。。。
又没看懂!
很闷的 太长了 不知道林奇为什么喜欢用劳拉邓恩?感觉她长得怪怪的
A. 升维版本的《穆赫兰道》,叙事空间层层叠加,影像空间不断延展,最终由高强度的情感完成字面意义的“洞穿”和对齐(因此即便被打上“烧脑”标签,它的内核也是高度感性与抒情的)。几乎集合了一切林奇钟爱的要素:吃人不吐骨头的好莱坞、堕落如百鬼夜行的美国城镇、在冥冥之中角力的纯粹的善与恶,和电影无限接近于梦的本质——不仅是形式上对意识迷宫的拟态,也是对其力量边界的承认与肯定。梦会醒,电影会结束,人总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但即便它只是一种逃离,却也能给我们直面心魔的勇气。真奇怪啊,明明是三个小时的阴暗爬行,我却被林奇的真诚所感动了,而从今往后,还有谁能像他一样拍电影吗?2022.1.28 Filmo 35mm
这么些年在资料馆看过最恐怖的一部,我日啊,三个小时的噩梦。不要尝试从噩梦中寻找意义和叙事,林奇的精神状态太美丽了。
太过迷离梦幻,故弄玄虚。。。。
扯了半天,原来还是在说一个现实中不满,在梦里满足自己愿望的梦,我当是什么,就梦境这点上,不如【穆赫兰道】,就故事背景来说,也没见什么新意,可见,不见得是大师,就每部作品都是上品,潜意识与前意识打仗,除了拍摄手法保持另类外,还有别的么?说实在话,这部真没什么看头,也不知道做什么分析
北影节资料馆午夜专场,筋疲力竭的三小时。林奇彻底放弃叙事,玩嗨了。梦中梦,戏中戏,一刀见底,深扎精神领域。劳拉邓恩不再是当年《我心狂野》里的金发长腿貌美女郎,岁月在她的脸上斑驳可见。好莱坞、星光大道、片场,会不禁联想到《穆赫兰道》,在支离破碎的梦里,《内陆帝国》的迷幻程度有过之而不及。前面漫长的台词对话和单调怼脸直拍的镜头,确实需要耐着性子去看,琐碎且不连贯的讲故事方式带来很高的理解门槛,所以不妨放平心态,着重感受做梦一样特别的观影体验,跟随着劳拉邓恩的脚步,在她惊恐万分的眼神里,鬼屋闯关式走过一个又一个空间,在电锯般尖锐的配乐下,迎接大荧幕中突然冲出来的一张张恐怖的脸,给快要昏睡过去的观众一个激灵,亦有趣味。#15th BJIFF#
林奇就林奇吧 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