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剧情介绍
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布米叔叔(Thanapat Saisaymar 饰)得了急性肾衰竭,因此回到乡里,边静养边等待死神来临。在乡下,他每天安静的吃饭、纳凉、看家人劳作,一个清凉的夏夜,布米叔叔、侄子和妻妹在院子里吃饭闲聊,布米叔叔去世很久的妻子竟然出现了,和他们诉说近况和多年思念,稍后,布 米叔叔失踪很久的儿子也出现了,变成了一只红眼黑毛猩猩,却没有人受到惊吓。阴阳相隔的几个人平静地拉着家常,平静的果园,平静的微风,蜜蜂每日平静的劳作,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那么自然,每个风景都早在那里了,每个故事都像一个梦…… 本片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秋去秋来挚爱家书还魂砂滨虎元气囝仔泡沫之夏笔墨纸砚拉米第二季夜战风云亚洲怪谈第二季母性契约少女管家街角少年第一季特搜组大吾救国的橘色部队爱有多远我在温州等你奔驰的大葱双刃遗产大作战阿尔涅的事件簿时髦老爹读书&喝酒桑格莉之夏米老鼠的捕鼠夹机甲英雄机斗勇者第2季爆笑悲剧王:笑着笑着就哭了第三季102真狗对手陛下在左,将军在右房间里的成年人
布米叔叔(Thanapat Saisaymar 饰)得了急性肾衰竭,因此回到乡里,边静养边等待死神来临。在乡下,他每天安静的吃饭、纳凉、看家人劳作,一个清凉的夏夜,布米叔叔、侄子和妻妹在院子里吃饭闲聊,布米叔叔去世很久的妻子竟然出现了,和他们诉说近况和多年思念,稍后,布 米叔叔失踪很久的儿子也出现了,变成了一只红眼黑毛猩猩,却没有人受到惊吓。阴阳相隔的几个人平静地拉着家常,平静的果园,平静的微风,蜜蜂每日平静的劳作,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那么自然,每个风景都早在那里了,每个故事都像一个梦…… 本片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秋去秋来挚爱家书还魂砂滨虎元气囝仔泡沫之夏笔墨纸砚拉米第二季夜战风云亚洲怪谈第二季母性契约少女管家街角少年第一季特搜组大吾救国的橘色部队爱有多远我在温州等你奔驰的大葱双刃遗产大作战阿尔涅的事件簿时髦老爹读书&喝酒桑格莉之夏米老鼠的捕鼠夹机甲英雄机斗勇者第2季爆笑悲剧王:笑着笑着就哭了第三季102真狗对手陛下在左,将军在右房间里的成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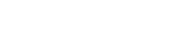
慢到了极致,还是耐心看完了,近期喜欢欧洲类似的电影2020.10.18//
什么ppt电影。。
给我看懵了
田野风光…………
几乎睡一个小时也不会影响观感的一部美术作品
#2018IFFR# Bright Future展映;塔林处女作单元。典型画意摄影,非常讲究堪称精美。故事很概念又几乎是宗教题材(该隐和亚伯+恐怖袭击往事),但也给了演员极大的发挥空间,老爷子简直是每一根皱纹都是戏,小哥全片没有一句台词,都完成得很漂亮。让人想起伯格曼和布列松。
比利时神片
filmart2018 day2第一片(又睡过了早上的片),明显感觉这些年世界电影的潮流早就转向轻叙事,故事常极简,重意境,制造一种留白的状态。而大陆电影还在为写/讲故事的基本功发愁,能抄个别人二十年前玩过的结构,仿佛就要飞上天了。所以电视剧更适合大部分中国观众。
节奏非常非常非常慢,但是在没有台词的安排中,又只有这样缓慢的镜头才能让情绪渗出来
把两个人的心理戏诠释的很好。大年初一看这个片子感觉有点压抑,不过场景很美,很多画面像油画。
厦航鹭上影院观影② >> 太难受😣 太难受的观影体验了 几乎无台词对白的一部电影 十分缓慢的推进 但氛围的铺陈太弱 时常某一刻进入 但又被立刻抽离 然后边看边疑惑下一秒到底会不会发生点让一切更清晰的行动 加上粗糙简陋的置景以及对我来说并无特别的拍摄手法 我真的喜欢不来也无法理解
太慢了 最多30分钟的内容拍了110分钟 干嘛呢这是
7.5
画面考究,城市或乡村丛林美学,自然音,闷日光的变化。沉默是一种靠近。
頗維米爾
有点沉闷
救赎,在最后一个镜头里么?在宅无限的春节假里,这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缓慢的节奏,优美的镜头,极简的布景,克制的叙事。足已!
想看看大家的讨论,结果没有讨论,连个长点的感想也没有。简介说是失手犯了罪,看不出是失手。准备把开头再看一下。最后应该是年轻人自首了,老人也因为包庇罪入狱了。但是正因为老人的收留包庇,年轻人才去自首。老人和年轻人在狱中作伴了。当然,老人关不了多久,他出去后也会常来看年轻人吧,孤独的老人有了情感寄托了
翻译成救赎更合适
没有对话的包容与温情相处,最终达到无言的双向救赎。镜头下宁静的乡村小屋与演员们的表情特写都令人印象深刻,一老一少两位角色的互动演绎深刻动人。